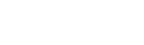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脍炙人口的那句话来形容当今的玉雕行业在合适不过了。纵观当前玉雕和制作,随着工具的改进,玉雕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,可以达到极其细致的工艺水准,一些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和玉石雕刻大师创作出了大量与时俱进、精美绝伦的玉雕作品。
然而,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粗制滥造的玉器,一些商家或者手艺人急功近利,任意挥霍手中宝贵的玉石资源,让人心痛不已。
进入20世纪后,随着勘探技术的极大提升,采掘工具的改进,人类采取玉石的能力越来越强,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和田玉的疯狂式采挖,青海格尔木玉料的发现、俄罗斯玉料的大量引入,还有韩国春川玉、岫岩河磨玉等透闪石玉料的发掘,造成了市场上玉料“过剩”的现象。
与此同时,伴随着珠宝玉石市场的蓬勃发展,玉石创造出的价值吸引大量的从业者进入,追求短期利益导致了玉石粗制滥造现象的丛生,包括像和田玉籽料这种稀有的宝贵资源也被随意的挥霍糟蹋了。
“玉厄”重现?
杨伯达先生曾指出,明末商品玉在追逐利润的经营思想的影响下,劣质粗工的玉器常常充斥着市场,其工艺、艺术水平大为降低,在玉坛上出现了重大缺陷和第一次扭曲。
清代乾隆皇帝由于自身是玉痴,十分关心玉雕,他曾六下江南,每到苏州均要去了解玉器加工行业的发展,他“发现专诸巷玉器有裁花镂叶,极其繁缛,或以玉之轻重论价,不肯多去瑕疵等特点”,乾隆帝称其为“玉厄”。杨伯达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我国玉器史上第二次扭曲失常。
可以看出,现在玉器行业的一部分现状跟明清时所谓的“玉厄”现象是如此的相像,那么现在是不是正在经历中国玉器史上第三次“玉厄”?再过几百年,后人手里握着这个时代的玉器,会如何评论这个时代的玉雕?
行业需要反省自查,国家也要有相应的行为,因为玉石不仅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,而且自古以来更是君子德行的物质载体,任意挥霍宝贵的玉料,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后人,更对不起中华绵延近万年传承下来的玉文化。
危机也是转机?
明中晚期虽然经历了第一次玉厄,但也出现了陆子刚等一批琢玉高手,其一些形制仍然影响着现在的玉雕界;针对第二次玉厄,乾隆帝提出了师古与画意等良方,以克其厄。
师古,无外乎就是仿制,但跟现在玉雕行业内的臆造、歪曲和拼凑完全不同,乾隆通过发掘出的古玉、传世玉器和宋朝《古玉图考》等进行系统仿制,并不是随意滥仿;画意也是有效的方法,玉雕跟绘画不可分割,当时清廷的造办处、如意馆、金玉作、启祥宫等机构汇集着那个时代最好的画家,包括像郎世宁等西洋画家也参与到了玉器设计。
而且,宫廷玉器的制作乾隆皇帝都要亲自对画稿进行审定,不满意还要修改,甚至推倒重来。这对当今的玉雕有两个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首先,绘画是玉雕的前提。看到玉雕二字,第一感觉玉主要是雕刻琢磨,这一点不假,但是,雕什么却是雕刻的基础,也就是绘画设计。现在行业内的从业人员,大部分都没有进行专门的绘画训练,先跟着师傅学,至于雕什么,都是师傅来定,感觉雕刻的手艺熟练了,就又跳槽或自己单干,然而基本功还未真正掌握,进而导致雕刻出来的作品缺乏美感,甚至不伦不类。一个好的玉雕作品,绘画设计和雕刻琢磨两者缺一不可。
其次,继承是玉雕的基础。不止是玉雕行业,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都需要创新,然而,创新不是凭空来的,更不是“天外飞仙”,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和学习。师古不是拟古,是为了更好的创新,乾隆工就是在师古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中国玉器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。
中国有8000多年的用玉历史,历朝历代的玉器都有不同的风格,玉器与当时的宗教信仰、政治制度、社会风俗息息相关,纵观玉器的发展历史,题材丰富,有很多值得细细挖掘的元素,而目前传承下来的还是远远不够。玉雕不是近10年或20年的玉雕,而是可以追溯8000年的玉雕,《资治通鉴》里开明宗义指出,“鉴于往事,而有资于治道。”玉雕更是如此,建议广大从业者系统学习中国古代传统玉器史,加深对中国玉文化以及玉器历史的了解。
玉器“首德次符”
那么,当代玉雕要往何处去?按照儒家经典说法,玉器“首德而次符”,君子比德与玉,君子佩玉的目的是要精进自我的德行。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,也就是中华文化的“轴心时代”,玉器与礼仪、德行密不可分,玉器超越了单纯的物质,而变为国家治国安邦、世人修身律己的重要载体。
到了汉代,玉器被官方垄断,变为皇家贵胄的珍宝,并把葬玉发展到了极致,金缕玉衣就是最典型的代表,这说明了汉代的人认为玉代表着一种不朽的精神,这是我国古代朴素的信仰;进入唐宋后,玉器逐渐世俗化,变为人们赏玩佩戴的饰品,但玉器题材仍然都是象征吉祥如意与美好生活的,这种延续一直到今天仍是主流。
从我国的玉器发展史可以看出,玉器一直以来都具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。“君子无故玉不离身”,玉不离身,首先要拥有玉,言外之意就赋予了玉石物质属性;“君子比德与玉”,意味着君子的德行要与玉石相符,五德、七德、九德、十一德都是为了以玉为参照物。